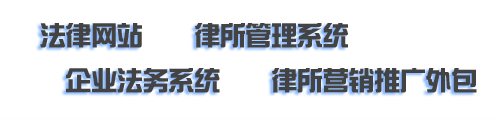常常有人将律师与医生做类比。比如,我常常告诉当事人,一个人得了病,大概有三种情况:一是不找医生也能治好,如感冒,吃几片感冒药,多喝些水,扛一扛就好了;二是必须找医生才能治好,如肝炎;三是找了医生也治不好,如晚期癌症。同理,一些案件不找律师也能赢,如证据确凿的债务案件;二是必须找律师才有可能赢,如知识产权案件;三是找了律师也不能赢,如肯定会判死刑的故意杀人案件。但是,律师与医生有一点关键之处没有可比性,就是社会需求性。
经济学有一个“盐的定律”,就是说人们吃的盐,不论在什么年代,不管它有多么贵重,人们也要吃,每个人都离不开,它的社会需求性是恒定的,永远不会改变。
我们以“盐的定律”来比较一下医生和律师的社会需求性就会发现,医生显然符合“盐的定律”,不管社会怎么变,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,从出生到死亡,都离不开医生。而律师在非发达的法治国家却不是。
首先,律师属于上层建筑范畴,不属于人们衣食住行,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经济基础。其次,律师业的历史,即使是在非常发达的西方法制国家,也不过几百年,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相比,不过是短暂的一瞬。我国律师业的历史更是短暂而命运多舛,中国古代专门和判案的官老爷“勾兑”的”讼师”,严格地讲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律师。直到民国以后,才在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有了真正意义的律师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新中国的律师大部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,所有的律师都停止执业,或被劳动改造或改行。直到1979年,才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恢复律师制度。
医生与律师的另一个区别是是否具有可替代性。一个人生了病,除了找医生,几乎没有别的可以替代的方法。头疼脑热,也许一扛就过去了,但如果得了肝炎,哪怕是得了阑尾炎,就必须看医生,否则就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一个人遇到了麻烦事,吃了官司,不一定非要找律师,而有多种渠道可以解决,包括合法渠道和非法渠道,比如,可以与对方自行和解,也可以花钱打通关系胜诉,甚至动用黑恶势力解决。
正是因为医生的不可替代性及律师的可替代性特点,一个医生的个人品德再坏,如果他想要在业内立足的话,医术必须要好,否则他就没有市场。而律师想要在业内立足,有充足的客户,在不良的法制环境下,不一定要有广博的法律知识,这一点与医生正相反。尤其在一个法制环境恶劣的地区,往往是对法律并不精通,却能熟练地运用社会”潜规则”办事的律师倒能够在当地律师界畅行无阻。
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,医务界即使再腐败,人们对医生收红包、开大处方等腐败之风再深恶痛绝,医生的患者量也不会减少。而律师如果不依法办事成风,将会毁掉整个律师业。哪怕一个满腹经纶,通晓法律、经济、外语的优秀律师,在一个十分恶劣的法制环境下,在一个律师业被毁掉的社会,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,为社会所不需。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,律师的历史断断续续加在一起不过几十年,这几十年与5000年相比,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,几乎都是人治的历史,在一个人治的社会,即使有律师,律师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太高。而真正意义的律师只能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。
在中国,律师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。律师仍属于“弱势群体”,除了为当事人据理力争,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外,还在为改变执业中的不公正境遇而进行自我维权。中国律师为什么属于“弱势群体”?我认为除了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刚刚实施,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,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以外,主要还有如下几个因素:
首先,中国律师从整体上讲还远离政治权力中心。有人会说,我们律师界不是也有人当上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了吗?但从总体上说,律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处于边缘地位,还远没有进入政治圈的主流位置。在中国,律师的政治角色还处于“刘罗锅”的尴尬地位——没你不行,有你碍眼。中国的政界距离西方律师出身的官员唱主角还相差太远。在美国参议院中,律师出身的参议员曾高达60%,美国历届总统中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居然占一半以上。而中国绝大多数律师与从政无缘,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等根本性的原因所造成,律师群体的从政渠道还远远没有打通,律师在政治圈内的声音还很微弱,只能说是敲边鼓,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。
其次,1996年出台的《律师法》将律师定位为“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,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”,取代了《律师暂行条例》规定的“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”,律师不再保持国家干部的身份,所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一律转制,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由“官”转为“民”,中国律师的角色定位逐渐实现了从公职性向民间性的回归。律师的民间职业角色其实就是法律的民间代言人。《律师法》对律师的重新定位较之过去是一大进步,但现实中律师还不具备强大的民间力量。日本、德国、加拿大等国将律师视为“在野法曹”,英美国家检察官其实就是国家雇用的控诉犯罪的律师。而中国律师不具有这样的地位。
再次,中国律师角色具有风险性。在中国,律师的外部生存环境不容乐观。即使每个律师都能严格自律,律师职业的风险性仍然很大。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在刑事辩护领域尤其明显,《刑法》第306条关于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的伪证罪,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,这一点属于非正常风险。在正常风险方面,律师很有可能因为疏忽、举证不力等因素而败诉。与医生特点相同的是,再好的律师也不敢保证他不犯错误,因为法律事务往往很复杂,律师总有由于知识结构等因素,某些问题把握不准,导致判断错误,给委托人带来不利后果的可能。我们不能饶恕的律师错误一般都是程序性的。律师只要在代理过程中不犯程序上的错误,对于实体的认识可以见仁见智,当然在法律上必须能自圆其说。香港不准大律师做广告,就是考虑到律师靠广告做大了以后,谁也不能保证这位律师今后不犯一个低级错误,从而一夜之间身败名裂。所以,律师宁可充当一个保守的角色,也不能“过把瘾就死”。
另外,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也是影响律师地位的因素之一。律师与委托人的法律服务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,这种法律服务关系是有偿的民事代理关系。当事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,购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,是一种消费行为。既然是消费,委托人对子律师的服务就有质量要求,甚至是苛求,因为委托人付出了,理所当然地要求物有所值。但是,律师有偿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往往很难界定,有其一般人无法掌握的内在规律。中国的普通民众法律意识还不强,法律素质还不高,势力强大的民间“潜规则”还在左右着法定规则,一些委托人往往情理不分,向律师提出法律服务之外的非分,甚至是非法的要求,一些律师还不能坚持原则地向他们说一声“不”!委托人对结果的期望值与现实影响案件结果的多种因素发生着矛盾,一些委托人往往将不利的结果迁怒于律师。律师或因服务不到位,或因律师与委托人缺少沟通,委托人对律师服务的不理解,都有可能被委托人投诉。委托人主要是看结果,律师在追求结果的同时更要看重过程。律师的对立面除了对当事人以外,有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委托人。因此,与委托人保持合理的距离,也是保护律师自身的必要措施。
正是因为中国律师有以上先天不足,又不具有医生“盐”一样的恒定社会需求性,任何一个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,任何一个法制环境中对律师的不利因素,都成为影响律师事业发展的外因。现在的问题是,一些律师杀鸡取卵,竭泽而渔,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丧失诚信、诋毁同行、搞不正当竞争、甚至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故意做伪证,指使当事人向法官行贿等,成为破坏律师赖以生存的法制环境的共犯。这一切,成为扼杀律师生命的内因。我们律师还左右不了外部法制环境,但是,我们应当洁身自好,严格自律,呵护本来就很脆弱的律师生命。
只有到了真正的法治社会,法律才能成为每一个公民日常消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律师才能变成“盐”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《远大前程》,描写一个名叫匹普的故事。苦命孤儿匹普小时候掩护了一个逃亡的囚徒,匹普长大之后,突然有一天福从天降,律师通知匹普说,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财主资助他到伦敦“接受上等人教育”,并说他将采可以继承大笔相当可观的财产,这个财主就是匹普救过的那个逃犯。逃犯临死前和匹普相见,匹普才知道这位财主是谁。逃犯资助匹普,是通过从事信托业的律师运作。《远大前程》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,那个时候英国就有了发达的信托业。而我国直到2001年4月才有《信托法》,许多国人至今还不知信托业为何物。从《远大前程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差距。书上说,美国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三种人——医生、律师、税务官。美国的律师已经变成了“盐”,真让中国同行羡慕。
文章来源:http://www.001law.com/file/2/6382.html